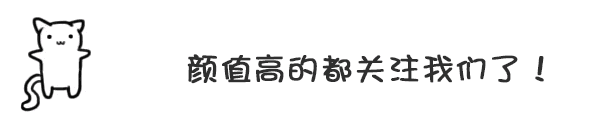

照片来源:John TonUnsplash
本文原载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12期
迷宫里的直播
牛莉莉
你每天都看新闻,总有人幸运,发了财,升了官,出了名,开着豪车,和美女生活在一起;也有人倒霉,死在乡下,进监狱,或者从地球上消失。这很奇怪。但你并不惊讶,因为报纸、网络、电视上的大部分新闻都是关于这种事情的。但有一天,你发现一篇新闻的主角是你的朋友。你一遍又一遍地重读这篇文章,就像你得了阅读障碍一样,读得很慢。你怀疑自己是否认识这样一个人。因为这则新闻,你的朋友变得遥不可及,你必须慢慢回忆起他的点点滴滴。你往后倒去,转椅的靠背挡住了你。你看着天花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个世界真是太奇怪了。
我的朋友叫黄虎,是我大学同学。他学的是冷战史,我学的是明朝史。冷战史是历史系的王牌,但他不喜欢。他说赫鲁晓夫、波兰危机、苏共二十大、杜鲁门、古巴导弹危机、铁幕演讲、马歇尔……书里的人物和事件虽然有趣,但都写在厚厚的《冷战史》里了。就算他没看完,结尾也印着结局。他每年都挂科,几乎不能毕业。我当时就不喜欢黄虎。当得知黄虎以微弱优势补考时,我在宿舍里感叹:“唉,明朝终于没落了!”毕业后,黄虎在一家很好的报社当记者,每天和那些没记下来的东西打交道。
我抬头望着天花板,上面仿佛投射着新闻标题,“知名记者与高中女生私奔”。黄虎当然不是什么知名记者,如果是知名记者,标题就不会写“知名记者”,而是直接写上他的名字。新闻里说,这个叫黄虎的记者平时喜欢上一些社交软件,装作成功人士去欺骗一些不谙世事的年轻女孩。这次他更进一步,直接绑架了一名高中女生。6月11日,两人见面后,黄虎在明知女孩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情况下,给女孩灌了酒,但表示开车不能喝酒。吃完饭,两人上了车,黄虎狂飙着开到了新疆和内蒙边境。女孩来自单亲家庭,父亲常年在外做生意,无暇管教女儿,直到一个月后才发现女儿离家出走。 焦急的父亲报了警直播用的什么笑声软件,但警方认为女孩已成年,是主动离家出走,并非人质,所以没有立案。父亲独自去找女儿。一周后,女儿终于回家。黄虎因长期旷工,已被单位开除。
我给黄虎打电话,他没接。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还是没接。几天后,我把这个消息忘了。后来,老同学聚餐的时候,我才想起这个消息。我随口一提,大家在回忆里谈起黄虎,好像突然变得敏锐而深刻,从过去的一两件小事分析出黄虎没落的根本原因。大家都说这家伙完蛋了。也有人感叹,其实黄虎在报社发展得很好,去年还获得了新闻奖的提名,如果获奖,将是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大家都说太可惜了。最后,有人总结了黄虎人生失败的原因,就是:聪明固然有用,但人这一生还是要脚踏实地,尽职尽责,这样才能不断向上爬。大家都说很有道理,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境界得到了升华。
聚会结束后,我再次给黄虎打电话,还是无法接通。回到家,看到家里温馨的灯光,听着妻子讲着工作上的琐事,我心里涌起一种幸福感:没有烦恼的生活真好!
时光飞逝。朋友上新闻的震惊已经完全消散。黄虎已经和我每天看到的新闻里的主角没有任何区别了。一年后,我再次拨打黄虎的电话,却无人接听。我从通讯录里删除了“黄虎”这个名字。我的生活里再也没有新鲜事了。即使“爆炸”、“凶杀”、“韩国政局动荡”、“美国火星探测器”等字眼充斥着媒体,我还是觉得世界没有变。我每天上班、回家、吃饭、睡觉,像孩子盼望假期一样盼望每个月八号的到来,因为那是发工资的日子。如果非要给我的时间一个形象的话,我想就是涟漪。无数个同心圆,内密外疏。在涟漪里,没有记忆与遗忘的区别,也没有今天与昨天的区别,因为每一个同心圆都是相似的。
一个冬日的傍晚,雪花纷纷扬扬,我独自走在街上。街道两旁霓虹灯亮起,路上行人寥寥。湿漉漉的路面映着红绿灯,一派萧瑟景象。我独自在街上徘徊。夜色渐深,雪越下越大,飘飘洒洒,有种磅礴之感。我的手冻得通红,但我却没有回家的意思,因为妻子出差了,回家太无聊了,还不如呼吸外面的冷空气。
我一个人不知不觉地走到江边。快过年了,桥上挂满了红灯笼。这座铁桥是清末洋务党修建的,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了。铁桥不能通车,只供行人行走。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铁桥上不见一个人影。桥上的红灯笼同时亮了起来。灯笼在风中疯狂摆动,打在铁桥上,发出“砰砰”的响声,不一会儿,许多灯笼就灭了。我一个人走在桥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河水,想着事情。我拿出手机,九点一刻,该回家了。我转身,看见远处有人在看河水。那人看了一会儿,顺着栏杆爬了上去。我赶紧过去。那人听到脚步声,从栏杆上下来。他站在黑暗中,喊道:“老刘!”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黄虎,有些吃惊,问:“你刚才干了什么?”
黄虎笑着说道:“我刚才在看河水和雪花,可是天太黑,看不清楚。”
我拿出一支烟,递给他一支,说:“人总有挫折,你何必总是往坏处想呢?”
“我知道我说我在看雪花,你不会相信。”黄虎笑着说。那天晚上的气温是零下五六摄氏度,但他依然很瘦弱,只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套,胡子好几天没刮了,看上去很苍老。我把手放在他的肩上,问他吃饭了吗。他说吃了。
我感慨的说:“我可不想在这儿碰到你。”
“你觉得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吗?”
“来吧,我们坐下吧。”
他摇头说道:“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我不想回去,你要是觉得冷的话,就先回去吧。”
我想黄虎肯定是想等我走了再跳进河里,我扶着他的胳膊说:“你觉得难得看到第一场雪,我却觉得难得看到你,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聊一聊。”
他想了想,说道:“好,那我们走吧。”
我和黄虎坐在酒馆里,我最好奇的当然是他和小姑娘私奔的事情,但我又不好意思说出来。万一他因为那件事不开心怎么办,我提起这件事,他又会躺在河边的栏杆上,那我就麻烦了。我们先说了各自的近况。黄虎说他现在在一家公司做文案,公司虽然小,但很受领导赏识,前途看好。我问他成家立业了吗,他摇摇头。我看他衣着单薄,想来他见了老同学,也不好意思说落魄。我们聊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无话可说了。他几次想走,我怕他又去河边,就紧紧抱住他不让他走。我们两个人无话可说,只好嗑瓜子喝啤酒。 喝了几瓶之后,他的脸色红润起来,眼睛明亮起来,他说:“我最多干到明年,已经攒了一万多块钱,等攒到两万,我就辞职。”那天我刚领了两万块钱的奖金,跟黄虎一对比,心里又开心起来。
我说:“这么好的工作,干嘛不干?毕竟我们都是本科毕业,找工作不容易。”
他摇了摇头。
他眼中的光芒又暗淡了下来。当我听到他谈论明年的计划时,我知道我想多了。他不会跳进河里。他可能真的在看雪花。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心里有些忐忑,想着该如何告别,他突然说:“两年前我出名了,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老熟人了。”
我知道他要提起那件事,所以我说:“是啊,那件事之后大家都很担心你。发生了什么事?”
他笑了。酒馆里光线昏暗。他靠在椅子上,点了一支烟,微笑着,很久没有说话。我俯身看着桌子,他的目光突然变得茫然。“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他说。
“什么?”
“我的意思是这首曲子是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是里赫特晚年在美国演奏的现场版本。”
这时,我才听见猜拳声和大声谈话声中隐约传来“叮叮咚咚”的声音。
黄虎笑了笑,仿佛沉浸在琴声之中。不知道是一曲结束,还是那喧闹声终于将琴声压制住了,再也听不到丝毫的音乐声。他掐灭了烟蒂,扔在了地上。 他说:“巴赫的音乐适合冬夜,单调、冰冷,似乎只有黑与白,就像几何图形。我见过的几何图形最完美的组合,不是在巴赫的音乐里,而是在迷宫里。几何图形之间完美的相似,让你陷入忘却。一开始没人喜欢迷宫,它让人焦虑。如果你每天都看着迷宫,从不试图走出来,你会逐渐喜欢它。它构图优美,令人惊叹。如果你想从里面找到出路,就会陷入眩晕。但如果你只是看着它,你就会知道,迷宫是世界上最稳定的构图。两年前,我曾试图走出一个迷宫。”
“然后你就上了头条?”我笑着说。我怕他跑题,就想给他点提示。黄虎,你快把那个可笑的故事讲给我听。
他笑了笑,不受我影响,继续用长音讲着。那天,我几乎能复述出他讲过的故事。这不是吹牛,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每天都会背东西,所以还是有些记忆的。另一方面,我也很兴奋,因为下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些故事原原本本讲给别人听。
黄虎说,两年前,他还在那家报社工作。说到新闻,他最爱“新”字,喜欢还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但工作了几年,他觉得无聊。冲天的火苗是新的吗?人的一生能经历多少次火灾?但他采访过十一起火灾。第一起是在一家大型超市,当时是晚上,黑烟冲天,像一只巨大的手,露出了红红的肉。一排消防车停在附近,水柱朝着火苗冲去,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毒烟。第二起是在城中村,第三起是在洗浴中心。对于之后的几起火灾,他只记得新闻稿的标题,至于现场,已经模糊不清。
没写完的和写完的有什么区别?黄虎很苦恼,他最初的激情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他每天都在平静地写下那些试图让别人吃惊的文字。凶杀、失控、车祸、某人的悲惨经历……他奔波在城市的各个地方,他熟悉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就像他熟悉一个叫做“K”的迷宫里的每一条线。但他从未走出去。
有一天,黄虎把这种苦恼跟领导分享了。领导压抑着自己的不耐烦,笑着告诉他:“小黄,是这样的,我们都这样。不光我们,你去问问你的同学,他们也这样。从学校到工作,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幻想。但生活不是这样,不像拍电影、演话剧,你要适应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角色转换。你的痛苦,就是你逃避了具体的生活,沉溺于幻想。生活是现实的,沉重的,乏味的。我们不能沉溺于幻想,那是不成熟的表现。”
黄虎听完这话,低着头不吭声。主任看了眼手表,翻了翻一堆文件,又看了眼手表。黄虎还是没说话。主任张了张嘴,大概是要命令他离开。黄虎说道:“张主任,这不是我要说的。”
张主任笑了笑,歪着头看向黄虎,眯着的眼眸中带着一丝嘲讽,“那你想说什么?”
黄虎说:“写新闻给我一种重复感。卡夫卡有一则寓言,说房间里有一只小老鼠,每天都按顺时针方向跑。有一天它被一只猫抓住了。它对猫说,你想吃掉我,我认命,不过我有个问题问你。猫说,什么问题啊?小老鼠说,我每天都在这个房间里按顺时针方向跑,可为什么我感觉房间越来越小,最后只有你的爪子那么大了。猫笑着说,如果你换个方向,也许房间会变大。导演,我想说的是,我每天都在各个场景之间奔波,但写东西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离地面十公里的深井里……”
张主任笑道:“你没听懂我说什么。”
“但我写新闻的时候总是有这种感觉。”
张主任又翻了翻文件,说:“新闻,就是这么回事。”
黄虎从领导办公室出来心情很郁闷,回到办公室后,发现了那幅画《K》。《K》的作者是美国人,师从著名幻觉艺术家埃舍尔。埃舍尔的作品后来被制作成风靡一时的游戏《纪念碑谷》,正是通过这个游戏,他了解了埃舍尔,也了解了那幅据说超越埃舍尔的画《K》。黄虎仔细地看着迷宫地图,迷宫地图气势磅礴,可当他试图从中寻找出路时,却陷入了眩晕之中。他想,人生就像这张迷宫地图,只要你不往里面看,它不会让你为难,可当你想看的时候,它却会让你头晕目眩。
黄虎顿时松了口气,又开始积极工作了。每当他觉得无聊、不甘心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迷宫。他告诉自己:永远不要正视迷宫,永远不要正视人生。
有一天下雨的时候,他又去了火灾现场。那是一家老电池厂,废料仓库发生爆炸,烧死了好几个仓库管理人员。在去现场的路上,他已经在脑子里写好了新闻稿,最后只需要核实几个数字就可以了。采访进行得很顺利,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相关部门的高层领导下达了指令,基层领导亲自到现场。黄虎之前采访过其中一位基层领导,那人一眼就认出了黄虎,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在火光和细雨中,黄虎和那位领导有说有笑,黄虎写稿很快。这是平常的一天。但黄虎回去的时候,突然想起十几年前这家电池厂发生过爆炸,当时原材料泄漏,渗入地下,污染了水源,当时整个城市陷入了恐慌。他赶紧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张主任。 张主任抽了根烟,想了想,说:“你放心吧。”
“但是如果水源被污染了怎么办?”
张主任笑着说:“这种事,有人操心,你就放心吧,还有相关部门在呢,放心吧,不能给政府添麻烦。”
黄虎有些着急:“可是,我们上新闻了……”
“新闻也不过如此。”张主任摆摆手。
黄虎回到家,仍旧思虑重重,一夜未眠。两天后,新华社刊登了有关水污染的新闻。全城人都疯了。黄虎也加入了抢购矿泉水的行列。他走在大街上,碰到每个店主都问:“你们有水吗?”店主们都无奈地摆摆手。
黄虎很疲惫,每天晚上都睡不好,他不想面对生活,可是水在哪里呢?他每天喝汽水、可乐、啤酒,已经很久没有喝过干净的水了。他感觉脑子里好像有很多人在吵架,其中一个声音在说:“黄虎,你真没用!”一天晚上,脑子里各种声音让他彻夜难眠,于是他用手机看直播。女主播叫小叶,穿着宽松的T恤,扎着马尾辫,身材高挑,面色白净,善于风骚微笑,但眼神有时也会变得冷淡,与笑容格格不入。黄虎觉得看直播挺好,能让他忘记烦恼,让脑子里的声音渐渐平静下来。小叶对着镜头哼唱了一首歌。黄虎问,这是什么歌?
“‘天涯何处无芳草’。”小野说。
黄虎说:“太美了。”然后,他就听着歌声睡着了。一天,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沙尘暴起,一排排的柳树在昏暗的天地间摇曳,风在怒吼,沙砾打在窗户上,像雨声一样。虽然门窗紧闭,但黄虎还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泥土味。黄虎心里空落落的。快下班的时候,张主任把黄虎叫到办公室,问他能不能开车。黄虎说,他不常开车。主任点头说:“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事,本来要我亲自去办,但晚上有聚餐,推不掉。”
黄虎说道:“主任,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主任笑着说:“你开着我的车去买点矿泉水吧,你去远的地方,附近县城肯定没水,别买散装的,一箱一箱的,散装的不好看,我要送给市里的领导,你自己也买点,路上小心点,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我给你放一天假。”
黄虎感动,张主任随时都能化危机为机遇,就算平日里给那些领导送名烟送酒,此刻也比不上送水有诚意,那一刻他又想到了卡夫卡的寓言,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老鼠,而主任就是那只笑眯眯地挠他的猫。
黄虎开着导演的车一直开到一座小土山脚下,下了车。此时,街边的路灯亮了起来。他抬头望向山坡,半山腰处有一栋小房子,昏暗的天地间,灯光亮着,像一只疲惫的眼睛。黄虎慢慢走上山坡,来到小房子门口,连抽了两口烟,然后敲门。开门的是肖野。肖野还穿着那件宽松的T恤,一脸茫然:“你是谁?”
黄虎说道:“我也算是你的粉丝了,我每天都看你的直播。”
肖野瞪大了眼睛,道:“粉丝?哦,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有天晚上你边看日落边直播唱歌,我觉得画面很美,就截图放大,看到上面的门牌号。”
小叶笑了笑,低头摇了摇头发,眯着眼睛看黄虎:“你是做什么的?”
“记者。”黄虎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这个身份显然勾起了小叶的好奇心,在商界人士的心目中,记者都是财经记者,而在这些一心想当网红的小姑娘的心目中,记者都是娱乐记者。小叶打开房门,快速的收拾了一下房间,房间里乱糟糟的,被子被推到了床脚,衣服散落在床上,靠墙放着两箱矿泉水。
小野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你来这里干什么?”
黄虎也不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说道:“我去找水,想找个人跟我一起去。”
肖野停下脚步,抬头说道:“你要做这样的节目吗?”
他笑着说:“是啊,你可以把我们找水的过程直播过来。”
黄虎说,每当回忆起这一幕,他都觉得很神奇。那天下午,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做抓猫,但他从来没想过往别的方向跑。没想到肖野完全是脑子简单的,听了他的想法后,居然爽快地答应了。黄虎顿时兴奋起来,他觉得自己摆脱了许久以来的无力感和无聊感,他又想到了迷宫图,这次一定要出去,不然永远都出不去。他邀请肖野吃饭。饭桌上,肖野一边喝啤酒,一边说:“我觉得你很有二年级生的风采。”
“什么是中二?”
小叶抿着嘴笑了笑,眼里的光芒如烟雾般飘渺,仿佛随时都会随风消散,“中二,就是初二。”
“初二?”
“是的。台湾有些校园剧的主角设定都是初二,相当于我们高二。高二意味着他还有些孩子气,还不够成熟。”小野说。
黄虎道:“那你呢?”
肖野哈哈大笑起来,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仿佛她的笑声是一团火球,她的身体是一堆易燃物。肖野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说:“我当然是中学生了,因为我是高二的。”
黄虎没想到肖野竟然是个高中生,带着一个高中生到处走,不但很不道德,而且很容易引起很多麻烦,他心里有些忐忑。
肖野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她接过黄虎面前的烟盒,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冷冷的说道:“你害怕了?”
“我不和未成年人混在一起。”他在大学时的文学偶像是安德烈·纪德,但那一刻,他不想成为一个变态。
小野说:“我已经成年了,中考了两年,没考上,虽然现在读高二,但是这他妈是艺术院校啊。”
“家里怎么办?”
小野说:“我是单亲家庭,爸爸常年在外做生意,你不用担心,你担心什么?”
黄虎说道:“我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答应跟我出去?”
肖野冷笑一声,道:“大叔,你这个人真是无趣,这可不好玩,你以为我是想占你便宜,还是我才十八九岁,精力旺盛,想跟你发生点什么事情?”
黄虎脸色通红,吃完饭,两人上了车,车上,小野又要直播了,她说没流量,让黄虎帮她开个热点,黄虎打开热点,把手机放在仪表盘上,就听见小野举起手机对着屏幕说:“各位朋友,我现在跟节目组做一个找水源的节目,好,谢谢,双击666,谢谢这位老板送的布加迪威龙,谢谢各位,把礼物发上来……”
车子快要离开市区的时候,黄虎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他下了车,从口袋里掏出“K”,掏出打火机点燃。肖野已经直播完了,问:“喂,大叔,你烧纸送小鬼吗?你们这个年纪的人,很讲究的。”
黄虎说道:“是照片,不过现在用不着了。”
他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关于迷宫的文章,文章里写道:“迷宫的第一条规则是用手摸着墙,朝一个方向走,最终就能走出迷宫。这条规则适用于单一迷宫,但如果是复杂迷宫,就可能陷入死循环。”
他上了车,说道:“我知道怎么去那里。”
路上的车很少,车灯照亮了路面,像一艘潜水艇沉入海洋最深处。黄虎打开车窗,外面微风徐徐,远处的群山起伏,像海怪的轮廓。黄虎没有留意路两边的路牌,只想顺着一个方向,走到路的尽头。
晚上十二点多,张主任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黄虎看得出来主任喝醉了,黄虎说,我快到路的尽头了。主任说,好好好,多买点,小心点,回来我请你吃饭。
黄虎挂了电话,肖野已经睡着了。凌晨五点左右,黄虎困了,从一个出口下了高速。一轮圆月从天上的云层中探出头来,冷冷的光芒照在路上。小路蜿蜒曲折,坑坑洼洼。黄虎找了个地方停车,看到一片圆圆的平地反射着光芒。黄虎以为那是水泥地,就想把车停在那里,可刚一拐弯,车子突然一抖,沉了下去。黄虎打开车门,借助天边的微弱光线,发现自己已经跌入了路边一片收割过的麦田里。他关上车门,在车窗上留出一条小缝隙,放下座椅,很快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面传来人声、狗叫声、牛叫声。他揉了揉眼睛,往窗外看去,果然停在了一户农家的田地里。下车一看,一片田地尽头是一望无际的群山,群山鲜红,十分美丽。他知道这是丹霞地貌,但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不远处是一池清水,周围树木繁茂,树下有一户人家。黄虎突然想起,昨晚看到的那片平整、反光的土地,其实就是这么一池水。幸好他没有把车停在那里,他打开车门,兴奋地说:“小爷,你看,世界是新的!”可是,小爷却不见了踪影。
黄虎走到小路上,环顾四周,喊道:“小爷!小爷!”远处,几个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直起身子看着他。黄虎上了车,费了好大劲才把车开回路上。他开到了一个农家院前的空地上。一个中年男子手拿铁锹,正好站在那里,好奇地看着黄虎的车。黄虎说:“不好意思,我先停在这里。”
中年男人笑着说:“没事,你停吧,市区停车要收费,这里随便停哪里都免费。”
黄虎下车递给男人一支烟,男人看了说:“好烟。”然后问黄虎来干什么。黄虎说:“逛逛。”
黄虎问道:“你看到跟我一起来的那个穿白色T恤的小女孩了吗?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那个男人说:“是的。我只是在早晨起床,那仍然是黑暗而阴暗的,我看到一个小女孩站在玉米田上,当她看到我时,她再次躲在玉米田里。我被吓到了。我害怕了,但我忽略了她,但她却在玉米田里看到了一个幽默,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乡村直播用的什么笑声软件,我却在一个乡下,我曾经是一个乡下的乡下,我曾经是一个乡下的旅程,我曾经是一段又见的,我曾经是一边逛了一段时光你说,我很放心。”
黄胡问:“县城是哪个方向?”
该男子指出并问:“怎么了?你有冲突吗?”
胡子说:“我不知道司机在他的身后回到车上不得不等到他完成加油并开车离开加油站,然后拿出手机。
消息说:昨晚我对我的电话打开了我的答案,我对我的回答很有趣。疲倦的窗户是坦白的,那一刻ird? 您的年龄可能会很简单,我的想法可以被您猜测,您是一个记者,您认为一切都不是老的。
…

